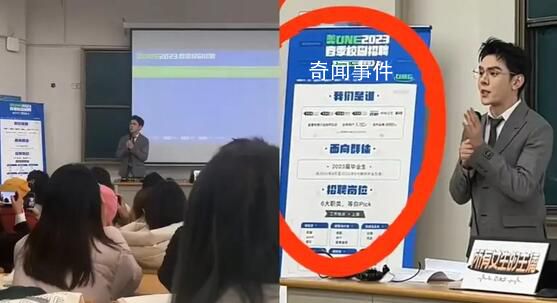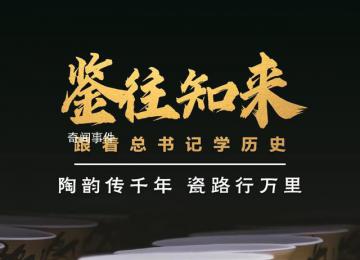如何認定李佳琦是否壟斷 底價協議是否涉嫌違反《反壟斷法》
導讀:今年雙十一才剛剛預熱,圍繞全網最低價的爭議已經出現。10月24日,京東采銷喊話李佳琦沖上微博熱搜。據媒體報道,京東采銷人員在朋友圈公開...

今年“雙十一”才剛剛預熱,圍繞“全網最低價”的爭議已經出現。
10月24日,“京東采銷喊話李佳琦”沖上微博熱搜。據媒體報道,京東采銷人員在朋友圈公開喊話李佳琦“二選一”。該工作人員表示,京東收到了品牌海氏的律師函,被投訴某款烤箱價格低于李佳琦直播間售價,違反李佳琦直播間要求品牌簽署的底價協議,并要求賠償巨額違約金。
該工作人員稱,該產品為京東自營商品,其價格低是因為京東自掏腰包進行了補貼,并質疑頭部主播有“二選一”行為。
隨后各方給出回應,李佳琦所在公司美ONE和涉及品牌方均否認了“底價協議”。不過“李佳琦公司美ONE合同細則曝光”“李佳琦直播間的底價協議合理嗎”等熱搜將事件推向高潮。
這種平臺補貼進行促銷,品牌方是否可以主張定價權?該事件中的“底價協議”是否涉嫌違反《中華人民共和國反壟斷法》(簡稱《反壟斷法》)?對此,新京報記者采訪了清華大學國家戰略研究院特約研究員劉旭。
關注1
如何認定頭部主播是否涉嫌壟斷?
劉旭表示,從上述事件中不難看出,直播帶貨行業的經營者與傳統電商平臺的分銷渠道存在價格競爭。從需求側和供給側看,如果兩者屬于同一相關市場,相比頭部電商平臺,無論是用戶數量、銷售額、分銷品類還是盈利能力,都比較難認定單一頭部主播有市場支配地位。
“正如媒體在報道中援引的某主播前員工的觀點,頭部主播之間也存在著激烈的競爭,只不過在這樣的競爭環境下,仍可能存在一些涉嫌違反《反壟斷法》的協議。”劉旭說,對于這些被業內人士視作涉嫌“壟斷”的行為,更應考慮適用《反壟斷法》有關禁止壟斷協議的規定,而非禁止濫用市場支配地位的規定,尤其是在直播帶貨與傳統電商平臺分銷很可能存在緊密的替代關系、構成同一相關市場時。
關注2
“底價協議”是否涉嫌違反《反壟斷法》?
此次事件中的爭議點,是品牌方與主播簽署的“底價協議”。如果品牌方與直播帶貨經營者簽訂了“底價協議”,承諾在限定促銷期間給予后者國內全網最低價格,這種“底價協議”是否涉嫌違反《反壟斷法》?
劉旭表示,這類縱向協議是否涉嫌違反《反壟斷法》,尤其是2022年修訂后的反壟斷法,需要進行個案分析,例如考察相關產品的市場份額、對消費者的具體影響等因素。對此,既要參考2022年版《反壟斷法》第十八條至第二十條的規定和《禁止壟斷協議規定》第十四條至第二十條的規定,還需要考慮《平臺經濟領域的反壟斷指南》的相關內容。
他認為,如果廠家和直播帶貨經營者沒有通過簽訂排他協議要求后者不推廣競品,并且事實上該直播帶貨經營者同時或先后分銷了多個廠商存在競爭關系的產品,且與這些廠家都簽訂了最惠條款,那么就有可能變相促成這些存在競爭關系的經營者之間出現價格協同,實現橫向限制競爭效果。這樣的做法會涉嫌違反2022年版《反壟斷法》的第十九條,其規定:“經營者不得組織其他經營者達成壟斷協議或者為其他經營者達成壟斷協議提供實質性幫助。”
關注3
平臺補貼進行促銷,品牌方是否可以主張定價權?
在媒體公布的律師函中,寫明京東與該品牌方簽訂《產品購銷協議》,合同中約定供貨價格——指甲乙雙方協商一致后乙方給甲方的產品供價。品牌定價權在乙方品牌方。而京東在合同履行過程中,多次違反合同約定,直接或間接修改產品銷售價,造成了該公司在與其他客戶合作中的被動違約,將產生巨額賠償的風險。
由平臺自掏腰包補貼進行促銷的行為,品牌方是否可以主張定價權?
對此,劉旭表示,這涉及轉售行為的認定問題。這也是適用《反壟斷法》規制限制最低轉售價格行為的一個關鍵問題。
他認為,如果涉及的商品所有權沒有發生變更,那么乙方作為相關產品的所有權人應該是可以選擇自主定價的,包括拒絕接受平臺補貼進行促銷。所以,上述律師函中的主張有其合理性。
同理,如果直播帶貨的經營者本身并沒有獲得其推廣產品的所有權,僅承擔廣告宣傳等推廣服務,并根據推廣績效獲取相應報酬,則通常也不具有被推廣產品的實際定價權。其充其量是《反壟斷法》意義上的“真代理人”角色,是品牌廠商的傳聲筒與“延長的手臂”。在這種情況下,上游廠商對從事直播帶貨的經營者所推廣價格進行限制,并不應被視作《反壟斷法》意義上的限制最低轉售價格。
比較復雜的情況是,上游廠商如果要求直播帶貨經營者至少成功代銷特定數量的產品,否則就需要后者承擔某些違約責任,導致事實上由后者與其共同承擔分銷價格偏離實際需求的后果時,那么至少在前述限定數量范圍內通過直播間代銷的產品仍舊可能會被視作為構成轉售行為,并可能因為設定最低轉售價格而違反《反壟斷法》。
下一篇:最后一頁
-
 如何認定李佳琦是否壟斷 底價協議是否涉嫌違反《反壟斷法》2023-10-30 11:16:46今年雙十一才剛剛預熱,圍繞全網最低價的爭議已經出現。10月24日,京東采銷喊話李佳琦沖上微博熱搜。據媒體報道,京東采銷人員在朋友圈公開
如何認定李佳琦是否壟斷 底價協議是否涉嫌違反《反壟斷法》2023-10-30 11:16:46今年雙十一才剛剛預熱,圍繞全網最低價的爭議已經出現。10月24日,京東采銷喊話李佳琦沖上微博熱搜。據媒體報道,京東采銷人員在朋友圈公開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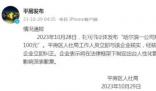 官方通報公司規定私聊微信罰款1002023-10-30 11:13:0510月29日,@平房發布 發布情況通報稱,10月28日,有網絡媒體發布哈爾濱一公司規定私聊微信每次罰款100元。哈爾濱市平房區人社局工作人員立
官方通報公司規定私聊微信罰款1002023-10-30 11:13:0510月29日,@平房發布 發布情況通報稱,10月28日,有網絡媒體發布哈爾濱一公司規定私聊微信每次罰款100元。哈爾濱市平房區人社局工作人員立 -
 牙醫實習生花1小時為自己拔智齒 網友:拔下的瞬間居然笑了2023-10-30 11:11:3510月27日,四川成都。牙醫實習生拿自己當病例,挑戰為自己拔智齒引關注,網友調侃是個狠人!當事人何同學稱,在學校時就有了這個想法,臨床
牙醫實習生花1小時為自己拔智齒 網友:拔下的瞬間居然笑了2023-10-30 11:11:3510月27日,四川成都。牙醫實習生拿自己當病例,挑戰為自己拔智齒引關注,網友調侃是個狠人!當事人何同學稱,在學校時就有了這個想法,臨床 -
 餐具收費大學生付1元直接帶走 餐具付了錢就是自己的2023-10-30 11:10:05近日,河北石家莊。大學生在餐廳吃飯時遇餐具收費1元,于是將4套餐具全打包帶走。當事人小張表示,結賬的時候詢問店員餐具可以帶走嗎,店員
餐具收費大學生付1元直接帶走 餐具付了錢就是自己的2023-10-30 11:10:05近日,河北石家莊。大學生在餐廳吃飯時遇餐具收費1元,于是將4套餐具全打包帶走。當事人小張表示,結賬的時候詢問店員餐具可以帶走嗎,店員 -
 湖北一運砂大貨車過自建橋時落水 或與大貨車載重過大有關2023-10-30 11:08:10據百姓關注最新報道,10月29日8時許,湖北省荊州市監利市荒湖農場附近一自建橋突然垮塌,一輛大貨車落入了水中。視頻顯示,落水大貨車裝滿
湖北一運砂大貨車過自建橋時落水 或與大貨車載重過大有關2023-10-30 11:08:10據百姓關注最新報道,10月29日8時許,湖北省荊州市監利市荒湖農場附近一自建橋突然垮塌,一輛大貨車落入了水中。視頻顯示,落水大貨車裝滿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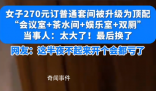 女子花270訂酒店套房竟有會議室 住這個房間半夜不起來開個會都虧了2023-10-30 11:07:1910月28日,吉林長春,女子和男友定了在某酒店定了一個普通的行政套間,結果被免費升級,推開門后發現房間非常大,除了臥室還有會議室、茶水
女子花270訂酒店套房竟有會議室 住這個房間半夜不起來開個會都虧了2023-10-30 11:07:1910月28日,吉林長春,女子和男友定了在某酒店定了一個普通的行政套間,結果被免費升級,推開門后發現房間非常大,除了臥室還有會議室、茶水 -
 大叔用廢棄筷子搭出微縮版黃鶴樓 將這些廢棄的筷子變廢為寶2023-10-30 11:05:33一次性筷子使用后,很多人直接將其丟棄,但在云南玉溪,一位村民展現了他的巧手,用廢棄的一次性筷子打造了微縮版黃鶴樓,以及玉溪當地的地
大叔用廢棄筷子搭出微縮版黃鶴樓 將這些廢棄的筷子變廢為寶2023-10-30 11:05:33一次性筷子使用后,很多人直接將其丟棄,但在云南玉溪,一位村民展現了他的巧手,用廢棄的一次性筷子打造了微縮版黃鶴樓,以及玉溪當地的地 -
 這英cos那英 讓人分不清楚真假2023-10-30 11:02:26一年一度的萬圣節即將到來,上海率先打響了第一槍,COS浪潮是一波接著一波,很多年輕人COS各路明星走在街頭,那是相當的搶眼。其中還有不少
這英cos那英 讓人分不清楚真假2023-10-30 11:02:26一年一度的萬圣節即將到來,上海率先打響了第一槍,COS浪潮是一波接著一波,很多年輕人COS各路明星走在街頭,那是相當的搶眼。其中還有不少 -
 幾塊錢的牙膏為何“銷聲匿跡” 牙膏為何越賣越貴2023-10-30 11:00:33這里是民生調查局,見人所未見,調查民生之變。關注你想關注的、你沒關注的,調查你想看的、未看到的。生活中,牙膏是必需品,但最近不少人
幾塊錢的牙膏為何“銷聲匿跡” 牙膏為何越賣越貴2023-10-30 11:00:33這里是民生調查局,見人所未見,調查民生之變。關注你想關注的、你沒關注的,調查你想看的、未看到的。生活中,牙膏是必需品,但最近不少人 -
 TST庭秘密何以“脫罪” 違反一事不能二罰?2023-10-30 10:58:49據報道,張庭涉嫌傳銷的原因是她經營的公司TST庭秘密涉嫌利用網絡從事傳銷活動。據了解,TST庭秘密是一家以化妝品為主打的公司,張庭是該公
TST庭秘密何以“脫罪” 違反一事不能二罰?2023-10-30 10:58:49據報道,張庭涉嫌傳銷的原因是她經營的公司TST庭秘密涉嫌利用網絡從事傳銷活動。據了解,TST庭秘密是一家以化妝品為主打的公司,張庭是該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