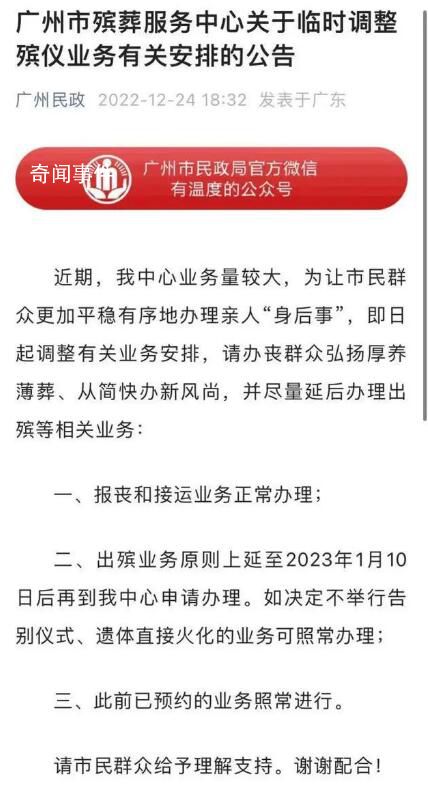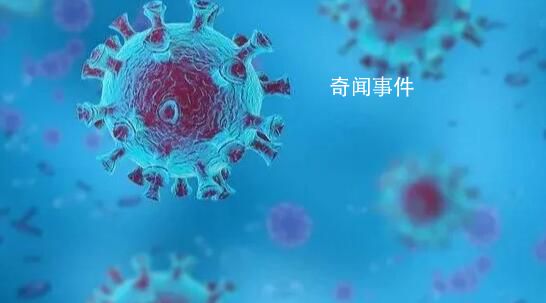廣州康鷺:30萬個踩縫紉機的人生
導讀:9月22日,廣州公布了鳳和片區(康樂村、鷺江村)規劃方案,備受關注的康鷺舊改再次成為焦點。一時間,幾乎所有跟服裝行業相關的人都在問:影...

9月22日,廣州公布了鳳和片區(康樂村、鷺江村)規劃方案,備受關注的康鷺舊改再次成為焦點。一時間,幾乎所有跟服裝行業相關的人都在問:影響了整個廣州制衣產業的鷺江村、康樂村真要拆了嗎?
對于康鷺到底有多少居民,似乎從沒有人真正“數”清楚過。多數口徑認為康鷺聚集了大概20萬~30萬的制衣行業從業者,95%以上是外來人口,本地村民加起來不到5000人。
外來人口中,湖北、四川、湖南、江西以及浙江溫州等地最多,尤其是來自湖北天門市、仙桃市、潛江市和荊州市監利縣等地外來人口占據多數,因此康鷺片區一帶又被稱為“湖北村”。
隨著一紙規劃的出臺,康鷺距離大規模拆遷改造又近了一大步,數十萬人的命運也隨之擺動,未來的康鷺,又將是什么樣的光景?
一、“這里可能是全國最大的招工市場”
“你在淘寶上買100塊以下的衣服,如果寄出地址是廣州,那么七成以上的幾率是康鷺生產的。”活躍在短視頻平臺上的康鷺網紅“服裝匠人老劉”如此告訴我。
老劉正在做一個系列短視頻,拍的是康鷺新招工廣場的情況,這個廣場8月份啟用,代替了原本站街招聘的形式,大棚“有瓦遮頭”。
新招工廣場上,服裝廠老板跟工人介紹手中的皮衣工藝
我來到新招工廣場的是一個雨天,早上七點,現場已經人潮涌動。夏末的九月正下著不小的雨,廣場內異常嘈雜。
工廠主們拿著各色衣服站在道路兩側,等待工作的人們從中間穿過,不時停下來細細看衣服的針線做工,雙方比劃幾句,一樁買賣可能就此達成。
人們從五湖四海來到康鷺,又從這里奔向四面八方
這里也是市集,但交易的不是衣服,而是一天的辛勞。
兩位仔細打量衣服做工的年輕女孩
“今天下雨人少了很多,昨天光是上午就來了四萬人左右。”海珠區人社局一位工作人員指著廣場旁邊的一排飲水機說:“以前都站在大街上招工,實在太亂了,現在我們給他們提供各種服務。”
一位當地人評論說,這(康鷺)可能是中國最大的短期勞務市場,“每天來市場找工作的就有幾萬人,你說我們村里總共有多少打工人。”
二、“我來這里賺錢,是因為這里能看到小蠻腰”
每一個來到康鷺的人都懷揣著不同的夢想
人潮總體繁忙又平靜,但難掩某種躁動的情緒,人群中偶爾有人爭執幾句,就吸引周圍的人聚集過去,伴隨著更大聲的起哄聲,氣氛開始變得緊張,保安們趕緊擠進人群把爭吵的雙方拉開。
對于打工人來說,長時間缺乏娛樂和社交的生活顯然過于沉悶,讓他們對一些能引爆激情的事件感覺特別興奮。
到招工廣場唯一目的就是掙錢,打上幾天或者十幾天的工,他們就能拿錢去尋找另外一段生活。
有些人混跡在網吧,有些人睡在天橋下,但大多數人在花完這筆短期收入后,又會回到招工廣場,尋找下一份工作,開始下一個循環。
走過雨后街頭的年輕人
每個出現在鷺江的人都有自己的理由,但不是每個來這里掙錢的靈魂都那么無趣。
“上次我在路上遇見一個阿姨,她說比起去白云的工廠,她更喜歡來康鷺打工,因為這里能看到廣州塔,讓她感覺自己生活在城里,我覺得她是一個對生活有追求的人。”
一起進村“采風”的同事憂子已經是康鷺的地膽(長期生活在本地,而對本地非常熟絡的人),她和老劉帶著我在如同迷宮一般的街巷里穿行,熟練得像一個村民。
憂子說,天氣好的時候,能在新招工廣場拍到廣州塔,但顯然雨天不是個好天氣,我只看到層層黑云,幾公里外的廣州塔已隱入云霧。
在康鷺幽暗小巷中打羽毛球的孩童
三、是走是留,是給每個人的人生命題
跟著憂子和老劉的腳步,我們進到了一個制衣廠。在這里,老劉要給老板做一個“訪談”,這也是他的新欄目,“主要問問大家對未來的計劃和期待,我相信這個視頻一定會火”。
早上9點多了,但工廠里只有寥寥幾個工位坐上了工人,老板早已習以為常:“他們每天干到深更半夜,早上什么時候來無所謂,反正是計件工資。”
網紅老劉正在訪問史老板
史老板是個90后,他2007年來康鷺當學徒,2012年開了自己的工廠,算得上打工族中的佼佼者。
談起新招工廣場,他說:“我不太喜歡去那里招工,我這里長期工比較多,短期工的技術比較沒譜,上次有個工人把我一批布都搞廢了,最后鬧到了派出所。”
“你的廠要是被拆了,你會有什么打算。”面對老劉的問題,史老板回答說:“我會在這里再找一個地方繼續干,總會有辦法的。”
面對這個問題,60后的老板龍哥顯然有不同的答案。
“我已經看了新塘的廠房,康鷺的廠房一般50到70一方,那邊才15到18一方。”龍哥說:“只要有車位有客戶,你去山溝溝里開廠都可以。”
江西人龍哥2013年來廣州,“洗腳上田”后來廣州發財,如今也算得償所愿。
他的廠房有600平方米,算得上康鷺的“頭部”,按他的話說,在廣州也算是“連鎖酒店”這個級別的。
龍哥來廣州十年,靠自己的奮斗當上了老板
龍哥顯然很有“覺悟”,他說:“我們這些來廣州賺到錢的人,要感謝人家的包容,現在政府需要,我們就要配合,當我們不能改變環境,就要去適應。”
“拆遷說了好些年,這次是不是真的要拆,還要拭目以待,不要大驚小怪,先把當下的事情做好。”
四、媲美互聯網大廠的收入,比廣州塔更晚熄燈的生活
不過,龍哥的工人阿雄并不準備死心塌地跟著老板去其他地方。阿雄一邊跟我聊天,一邊熟練地車著手中的皮料:
“我跟老婆在這里干了三年,如果工廠要搬,我就不一定跟著老板走了,小孩子現在大了,也許我會回老家去陪讀。”
制衣廠的工人阿雄和他的妻子
比起高學歷打工人云集的996互聯網大廠,制衣廠的勞動時間和收入都有得一拼。
制衣工靠計件工資,像阿雄這樣的熟練工一個月能掙兩萬以上,但每天工作時長經常在十四五個小時。
每天晚上廣州塔熄燈后,康鷺卻依然燈火通明,零點后的康鷺比珠江新城還要光彩照人。
被人津津樂道的還有外來工中的“臨時夫妻”現象,阿雄主動聊起這個話題:“我們是倆夫妻都在這里,但這邊臨時搭伙過日子的也非常多,畢竟出門在外嘛。”
聽到阿雄的話,他身邊的工友都意味深長地笑了。
長時間埋頭制衣的機械式工作并不是件讓人愉快的事情。在網上,“我在康鷺踩縫紉機”是個熱門話題,曾在此打工的人們用各種段子調侃這段生活。
孤獨、窘迫、欺凌……異鄉的生活總有許多不如意。
康鷺的街頭,每一個人的生計都離不開制衣
今年上半年,南方人物周刊的記者以打工者的身份在康鷺體驗生活并寫了篇稿子,標題就叫做《生活在別處,反正不在康鷺》。
三十萬雙踩動縫紉機的腳,三十萬在針尖上謀生的人。我總相信,無論在何處討生活,他們都應該值得有自己更美好的生活。
下一篇:最后一頁
-
 廣州康鷺:30萬個踩縫紉機的人生2023-10-04 20:19:539月22日,廣州公布了鳳和片區(康樂村、鷺江村)規劃方案,備受關注的康鷺舊改再次成為焦點。一時間,幾乎所有跟服裝行業相關的人都在問:影
廣州康鷺:30萬個踩縫紉機的人生2023-10-04 20:19:539月22日,廣州公布了鳳和片區(康樂村、鷺江村)規劃方案,備受關注的康鷺舊改再次成為焦點。一時間,幾乎所有跟服裝行業相關的人都在問:影 -
 張杰回應謝震業 我們都為你們驕傲鼓掌2023-10-04 20:18:20張杰近日在社交媒體上熱情回應了謝震業的舉動。謝震業,中國田徑隊的耀眼運動員,在杭州亞運會男子100米接力賽中勇奪桂冠,為他的隊友們點
張杰回應謝震業 我們都為你們驕傲鼓掌2023-10-04 20:18:20張杰近日在社交媒體上熱情回應了謝震業的舉動。謝震業,中國田徑隊的耀眼運動員,在杭州亞運會男子100米接力賽中勇奪桂冠,為他的隊友們點 -
 黃曉明因被嘲笑英文去演了英語老師 引發了廣泛的熱議和討論2023-10-04 20:16:4910月4日報道,在最近一次公開的談話節目中,演員黃曉明分享了他在參演電影《中國合伙人》時的經歷。這段經歷源自他曾因英文被嘲笑,而決定
黃曉明因被嘲笑英文去演了英語老師 引發了廣泛的熱議和討論2023-10-04 20:16:4910月4日報道,在最近一次公開的談話節目中,演員黃曉明分享了他在參演電影《中國合伙人》時的經歷。這段經歷源自他曾因英文被嘲笑,而決定 -
 中國游客遇襲身亡:源計劃凌晨回國2023-10-04 20:16:1610月3日,泰國曼谷暹羅百麗宮購物中心發生槍擊事件,南都記者從中國駐泰使館獲悉,一名中國公民不幸遇難,另有一名中國公民受傷。4日上午,
中國游客遇襲身亡:源計劃凌晨回國2023-10-04 20:16:1610月3日,泰國曼谷暹羅百麗宮購物中心發生槍擊事件,南都記者從中國駐泰使館獲悉,一名中國公民不幸遇難,另有一名中國公民受傷。4日上午, -
 中國游客遇襲身亡:原計劃凌晨回國2023-10-04 20:15:1410月3日,泰國曼谷暹羅百麗宮購物中心發生槍擊事件,南都記者從中國駐泰使館獲悉,一名中國公民不幸遇難,另有一名中國公民受傷。4日上午,
中國游客遇襲身亡:原計劃凌晨回國2023-10-04 20:15:1410月3日,泰國曼谷暹羅百麗宮購物中心發生槍擊事件,南都記者從中國駐泰使館獲悉,一名中國公民不幸遇難,另有一名中國公民受傷。4日上午, -
 網友開曬國慶返程后備箱 瓜果蔬菜各種土特產就連雞鴨都得掛車上2023-10-04 20:13:3610月4日,距離國慶長假結束只剩3天,各地網友們紛紛曬出自己返程的后備箱,瓜果蔬菜、各種土特產,就連雞鴨都得掛車上。有很多網友反映自己
網友開曬國慶返程后備箱 瓜果蔬菜各種土特產就連雞鴨都得掛車上2023-10-04 20:13:3610月4日,距離國慶長假結束只剩3天,各地網友們紛紛曬出自己返程的后備箱,瓜果蔬菜、各種土特產,就連雞鴨都得掛車上。有很多網友反映自己 -
 “國慶參加完23場婚禮,我破產了”2023-10-04 20:11:30國慶假期尾聲已至,許多打工人已經隱隱有了上班前綜合征發作的征兆。很嚇人,我感覺還沒干什么呢,怎么假期余額就奔著清零去了!不過這樣說
“國慶參加完23場婚禮,我破產了”2023-10-04 20:11:30國慶假期尾聲已至,許多打工人已經隱隱有了上班前綜合征發作的征兆。很嚇人,我感覺還沒干什么呢,怎么假期余額就奔著清零去了!不過這樣說 -
 “大聰明”又堵路上?提前3天還堵2023-10-04 20:10:0810月4號,網絡上熱傳著一個熱搜:一些大聰明們提前三天出發,想要避開假期結束時的交通擁堵,結果還是在路上被堵了個正著。這讓網友們不禁
“大聰明”又堵路上?提前3天還堵2023-10-04 20:10:0810月4號,網絡上熱傳著一個熱搜:一些大聰明們提前三天出發,想要避開假期結束時的交通擁堵,結果還是在路上被堵了個正著。這讓網友們不禁 -
 7歲男孩偷拿錢買蘿卜刀被送派出所 見到警察后男孩便意識到了問題的嚴重性2023-10-04 16:48:139月27日晚,一位母親帶著孩子來到秦集派出所稱:孩子拿了家里的錢去買了玩具,教育無果,請求警察幫忙。見到警察后,男孩便意識到了問題的
7歲男孩偷拿錢買蘿卜刀被送派出所 見到警察后男孩便意識到了問題的嚴重性2023-10-04 16:48:139月27日晚,一位母親帶著孩子來到秦集派出所稱:孩子拿了家里的錢去買了玩具,教育無果,請求警察幫忙。見到警察后,男孩便意識到了問題的 -
 哈爾濱組團到南京賣房 成交量為零2023-10-04 16:46:59從9月9日到9月11日,幾排藍色展臺顯眼地占領著南京市江北印象匯廣場的西側入口。行人經過時即便不留神,也能發現這里正在舉辦一場房產推介
哈爾濱組團到南京賣房 成交量為零2023-10-04 16:46:59從9月9日到9月11日,幾排藍色展臺顯眼地占領著南京市江北印象匯廣場的西側入口。行人經過時即便不留神,也能發現這里正在舉辦一場房產推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