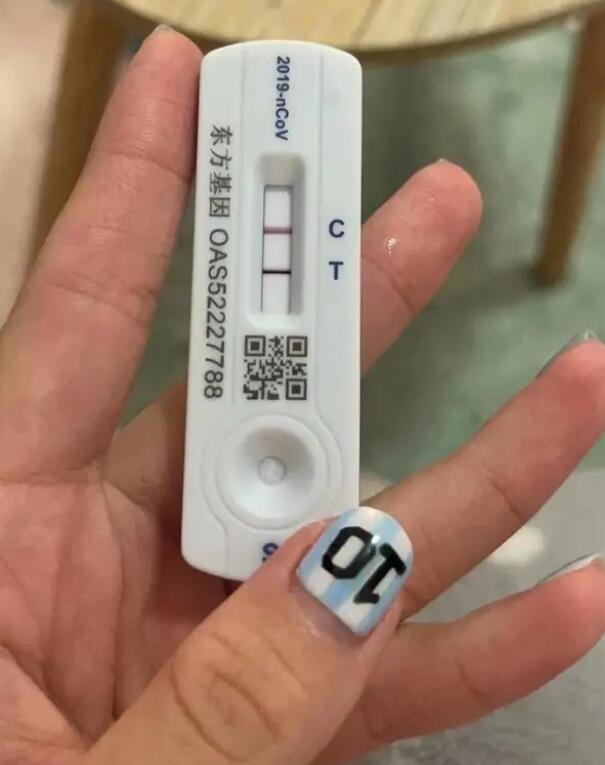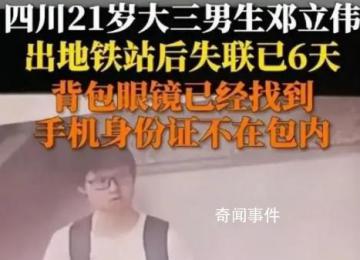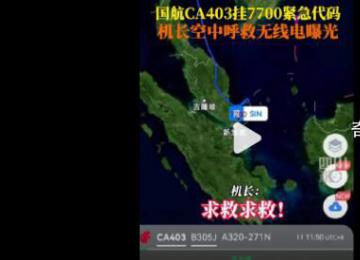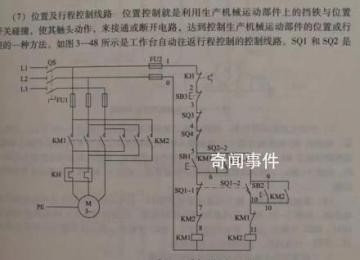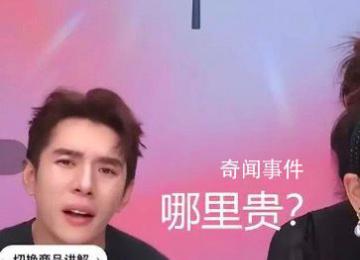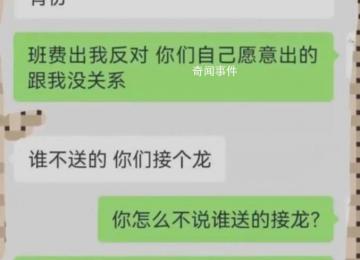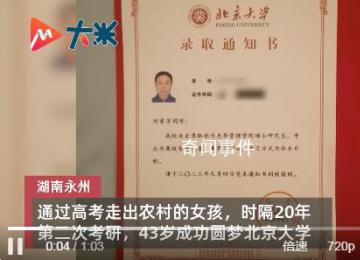媒體:吳謝宇還有機(jī)會(huì)嗎?
導(dǎo)讀:5月19日,吳謝宇弒母案在福建高院二審開(kāi)庭。在此之前,他一審被判死刑立即執(zhí)行,隨后提起上訴。在二審中,吳謝宇依然表現(xiàn)出強(qiáng)烈的求生欲望
5月19日,吳謝宇弒母案在福建高院二審開(kāi)庭。在此之前,他一審被判死刑立即執(zhí)行,隨后提起上訴。在二審中,吳謝宇依然表現(xiàn)出強(qiáng)烈的求生欲望,哭求法庭給他一次機(jī)會(huì),用余生來(lái)贖罪。二審辯護(hù)律師申請(qǐng)為吳謝宇作司法精神病鑒定,但法庭未當(dāng)庭作出是否啟動(dòng)的決定。
除此之外,辯護(hù)律師還提到一個(gè)很重要的辯護(hù)理由,擴(kuò)大性自殺。吳謝宇的行為是否屬于擴(kuò)大性自殺?如果認(rèn)定為擴(kuò)大性自殺,是否會(huì)影響他的刑事責(zé)任?吳謝宇弒母的行為,是否必須用死刑立即執(zhí)行來(lái)體現(xiàn)報(bào)應(yīng)?這些問(wèn)題,都是本案主審法官要直面的,也值得我們思考。

一、擴(kuò)大性自殺
擴(kuò)大性自殺一般是指自殺者在抑郁情緒的影響下,考慮到自殺后親人的不幸或痛苦,從同情和憐憫的角度出發(fā),先將親人殺死后再自殺。不久前媒體報(bào)道,某地一母親用繩帶將自己和女兒纏縛后,投河溺水身亡,其中兩個(gè)女兒大的8歲,小的年僅2歲。此案后續(xù)調(diào)查還在開(kāi)展,如果查明母親本身嚴(yán)重抑郁,那這種情況就符合擴(kuò)大性自殺的表現(xiàn)。
擴(kuò)大性自殺會(huì)給案件偵辦帶來(lái)兩個(gè)問(wèn)題:一是有人死亡,需要明確案件性質(zhì),確定是自殺、他殺還是意外。二是當(dāng)自殺者自殺成功時(shí),需要確定死亡的先后順序和真實(shí)原因;而當(dāng)出現(xiàn)自殺未遂的情況時(shí),又需要對(duì)自殺者的精神狀態(tài)做出司法鑒定。在吳謝宇案中,如其所述,還出現(xiàn)了“自殺者打消自殺念頭”的情形,此時(shí),對(duì)他的精神狀態(tài)認(rèn)定就更加復(fù)雜了。
一般而言,擴(kuò)大性自殺的行為人在殺人前一定存在強(qiáng)烈的自殺念頭,這是判定此類案件性質(zhì)的重要依據(jù);而在殺人后隨即自殺,則體現(xiàn)了擴(kuò)大性自殺案件的內(nèi)在邏輯。畏罪自殺與此不同,兇手在作案之前并不存在強(qiáng)烈的自殺念頭,作案后也不一定會(huì)立即自殺,往往走投無(wú)路了才會(huì)選擇自殺。
反觀擴(kuò)大性自殺的當(dāng)事人,在案發(fā)前可能多次嘗試自殺或準(zhǔn)備遺書(shū),同時(shí)在殺人后自殺意圖堅(jiān)決。當(dāng)然,也有關(guān)于抑郁癥患者攜子自殺時(shí),因看到孩子拼命掙扎而突然醒悟,進(jìn)而搶救孩子并放棄自殺的報(bào)道。無(wú)論如何,強(qiáng)烈的自殺念頭至少持續(xù)到殺人時(shí)是擴(kuò)大性自殺的一個(gè)重要特點(diǎn),把握這個(gè)特點(diǎn)才能避免放縱犯罪。
國(guó)內(nèi)通說(shuō)認(rèn)為,對(duì)于患有抑郁癥的擴(kuò)大性自殺者,其實(shí)施犯罪是在強(qiáng)烈的自殺念頭與病理性抑郁情緒支配下進(jìn)行的,其辨認(rèn)、控制能力下降或喪失,因此可評(píng)定為限制責(zé)任能力或無(wú)責(zé)任能力。在司法實(shí)踐中,也有多起判決做出了對(duì)行為人有利的認(rèn)定。那么,吳謝宇的行為是否構(gòu)成擴(kuò)大性自殺呢?
根據(jù)一審判決認(rèn)定的事實(shí),“被告人吳謝宇悲觀厭世,曾產(chǎn)生自殺之念,其父病故后,認(rèn)為母親謝某某生活已失去意義,于2015年上半年產(chǎn)生殺害謝某某的念頭,并網(wǎng)購(gòu)作案工具”。在一審中,吳謝宇稱,自己與母親相處的過(guò)程中長(zhǎng)期處于壓抑狀態(tài),他想自殺,又因?yàn)閾?dān)心“自己先走了,母親會(huì)崩潰痛哭”,于是殺害母親。這些細(xì)節(jié)基本符合擴(kuò)大性自殺的特征,因?yàn)閿U(kuò)大性自殺又名“家族自殺”,行為人殺害的往往都是自己最親近的人,比如子女、配偶等,往往出發(fā)點(diǎn)都是“我死了,你也受罪,你也好不了,不如一起去死”。
但吳謝宇的另一些行為,又與典型的擴(kuò)大性自殺矛盾。比如,一審公訴人曾經(jīng)問(wèn)他為何要在入戶門口裝攝像頭和報(bào)警器,他供認(rèn)說(shuō)是為了觀察何時(shí)被人發(fā)現(xiàn),被人發(fā)現(xiàn)他就打算結(jié)束自己的生命。這種擇機(jī)自殺的心態(tài)與擴(kuò)大性自殺并不吻合。根據(jù)他的陳述,在得手之后,他突然“頓悟”,失去了自殺的勇氣。這也使得擴(kuò)大性自殺的認(rèn)定有一定難度。
辯方辯稱,一些精神障礙者遇到重大事件時(shí),患者會(huì)突然清醒,終止自己的危害行為。這理由不假,前文也提到抑郁癥患者攜子自殺時(shí)突然清醒的例子。但是吳謝宇為何“頓悟”,為何清醒?為何在犯罪過(guò)程中如此心思縝密,并且體現(xiàn)出極強(qiáng)的反偵查意識(shí)?這是不是事后找理由?他現(xiàn)在如此強(qiáng)烈地想活,是否真的曾想過(guò)要自殺?他的求生欲望是一向如此,還是因?yàn)槟赣H的死亡激發(fā)的呢?這些疑問(wèn)還需要進(jìn)一步證明。
二、吳謝宇案發(fā)時(shí)的精神狀態(tài)
千古艱難唯一死,吳謝宇在入獄之后渴望生,在弒母之后也沒(méi)有選擇自殺,他有他的理由。但是,在事后判斷他的行為是否屬于擴(kuò)大性自殺的時(shí)候,自殺本身就成為重要根據(jù)。因此,他在案發(fā)后表現(xiàn)出的自私和怯懦,他的逃亡和茍活,呈現(xiàn)出與擴(kuò)大性自殺不相吻合的特征。
吳謝宇弒母,到底是不是擴(kuò)大性自殺呢?這個(gè)辯護(hù)理由很重要,但也可以說(shuō)“意在沛公”。因?yàn)槎忁q護(hù)人提出的辯護(hù)意見(jiàn)是,吳謝宇在案發(fā)時(shí)重度抑郁癥發(fā)作伴精神病性癥狀,作案時(shí)辨認(rèn)、控制能力下降或喪失。我理解,這個(gè)辯護(hù)意見(jiàn)兼顧了被告人的精神狀態(tài)和犯罪心理。也就是說(shuō),即使法庭不認(rèn)定擴(kuò)大性自殺,也應(yīng)該考慮吳謝宇當(dāng)時(shí)的精神狀況。這是在一審判決中也確認(rèn)的“悲觀厭世,曾產(chǎn)生自殺之念”,這個(gè)事實(shí)可能會(huì)對(duì)吳謝宇的刑事責(zé)任產(chǎn)生影響。
吳謝宇案發(fā)當(dāng)時(shí)的精神狀態(tài)到底如何?是否需要對(duì)他做精神病鑒定?這是從一審開(kāi)始就被反復(fù)討論的問(wèn)題。二審辯護(hù)人申請(qǐng)對(duì)吳謝宇做精神鑒定,有個(gè)重要原因是其父親家族有精神病史。對(duì)此,檢方確認(rèn)吳謝宇的兩位姑姑分別患有精神分裂癥以及智力障礙,但根據(jù)有關(guān)證人的證言證詞,檢方認(rèn)為上述兩位親屬的精神病癥是外力刺激所致,而非家族遺傳,因此不建議多此一舉。
檢方不愿對(duì)吳謝宇啟動(dòng)精神鑒定,是可想而知的——一旦鑒定意見(jiàn)有利于行為人,他就有可能不負(fù)刑事責(zé)任或者限制刑事責(zé)任。這樣一來(lái),鑒定人和法官就將面臨來(lái)自案件當(dāng)事人和社會(huì)輿論的巨大壓力。但一般情況下,如果行為人有醫(yī)院門診、住院病歷記錄證明有精神異常史的;或者有精神病家族史的;或者雖沒(méi)有明確病史,但有證人反映其明顯異于常人、頭腦笨拙、動(dòng)作幼稚、有抽搐史等的,再結(jié)合行為人的目的、動(dòng)機(jī)、方式、過(guò)程有悖常理,一般應(yīng)當(dāng)啟動(dòng)精神病鑒定。再看吳謝宇案的情況,兩位近親都受外力刺激導(dǎo)致精神病癥,這個(gè)概率未免也高了點(diǎn)。從常理看,可以啟動(dòng)精神鑒定。
其實(shí)從醫(yī)學(xué)角度來(lái)說(shuō),持續(xù)抑郁的人因受到特定事件的刺激,導(dǎo)致抑郁情緒急劇加重而做出殺人和自殺舉動(dòng),可以說(shuō)是事出有因。而在法律的層面,如果行為人本身的主觀惡意不大,且造成的社會(huì)危害較小,給予過(guò)重的刑罰既不利于對(duì)其改造,也不利于社會(huì)示范。
三、可殺可不殺嗎?
吳謝宇一審被判處死刑立即執(zhí)行。二審是否有可能改判為死緩加限制減刑,是否也能體現(xiàn)刑罰相當(dāng)呢?我國(guó)的死刑政策是——雖然還不能廢除死刑,但應(yīng)逐步減少,凡是可殺可不殺的,一律不殺。為什么還不能廢除呢?這可能是死刑唯一的正面意義,它能實(shí)現(xiàn)報(bào)應(yīng)從而平復(fù)受害者及其家屬的仇恨。
減少死刑的第一個(gè)理由是實(shí)用主義的,那就是死刑可能會(huì)錯(cuò)殺。當(dāng)然本案沒(méi)有這個(gè)風(fēng)險(xiǎn)。
第二個(gè)理由還是功利的,就是威懾犯罪的關(guān)鍵在于懲罰的必然性和合理性,而不是懲罰的強(qiáng)度。壞人是要懲罰的,可以用自由刑去罰,嚴(yán)重的可以無(wú)期加限制減刑,但是沒(méi)必要用死刑。因?yàn)樗佬瘫旧聿⒉荒苡行У卣饝胤缸铮瑩Q言之,殺人殺不出敬畏心。但這一點(diǎn)和人們的直覺(jué)并不相符。大部分人仍然覺(jué)得,只要多死一些壞人,這個(gè)世界就會(huì)變好。在吳謝宇案的評(píng)論中,也有大量的聲音說(shuō)“謊話連篇趕緊殺了”。
第三個(gè)理由,就是死刑本身的正當(dāng)性,這個(gè)問(wèn)題見(jiàn)仁見(jiàn)智。總之,我國(guó)《刑(八)》廢除了13個(gè)罪名的死刑,《刑(九)》廢除了11個(gè)罪名的死刑,我國(guó)的死刑政策就是要確保死刑這一最嚴(yán)厲的刑罰,真正只適用于極少數(shù)罪行極其嚴(yán)重、不堪教育改造的犯罪分子。那吳謝宇是這樣的人嗎?
從媒體刊登的吳謝宇獄中來(lái)信和母親生前日記可以看出,吳謝宇的原生家庭負(fù)擔(dān)很重,父親家族貧窮又有精神病史,母親家族貧窮父母都是盲人。這兩個(gè)人都是家族中唯一的大學(xué)生,需要承擔(dān)照顧整個(gè)家族的重任。吳謝宇只能依靠學(xué)習(xí)來(lái)出人頭地,但父親的去世成為影響他和他母親的一個(gè)“關(guān)鍵的轉(zhuǎn)折點(diǎn)”,從那時(shí)起,他“一步步踏上了自我毀滅的不歸之途”。開(kāi)導(dǎo)母親似乎是吳謝宇難以完成的任務(wù)。面對(duì)無(wú)力掙脫的控制與壓力,只有死才是解脫。
也許這個(gè)故事原本的結(jié)局是吳謝宇弒母后自殺,由是成為一場(chǎng)匆匆謝幕的悲劇。然而吳謝宇并沒(méi)有去死,他逃亡并茍活于世,即使在法庭上,他也哭著求法官讓他活著贖罪。故事變得失控,說(shuō)好去死的人沒(méi)有去死,讓我們不得不一層一層剝開(kāi)洋蔥,發(fā)現(xiàn)人心和社會(huì)最深處的秘密。
故事還有另一個(gè)更傷感的情節(jié)。在吳謝宇的獄中來(lái)信里,他提到,他作案后才慢慢意識(shí)到,當(dāng)他陷入絕望時(shí),母親其實(shí)正在慢慢走出來(lái)。母親的鄰居說(shuō),在出事之前她的狀態(tài)正在好轉(zhuǎn),“我跟她聊天,整個(gè)人的精神已經(jīng)有變化了,講話時(shí)的語(yǔ)氣都比較輕松”。有位網(wǎng)友評(píng)論說(shuō),這才是本案讓人感到最絕望和最無(wú)力的時(shí)刻。我同意這個(gè)判斷,如果時(shí)光能重來(lái),是否能夠告訴那個(gè)少年,“別放棄,其實(shí)你還有機(jī)會(huì)”?
-
 深圳交通局官方賬號(hào)禁止網(wǎng)民評(píng)論2023-09-16 16:51:09近日,深圳市交通運(yùn)輸局對(duì)網(wǎng)民申請(qǐng)公開(kāi)北極鯰魚(yú)調(diào)查情況一事作出不予公開(kāi)的回復(fù),很快便引起了社會(huì)大眾對(duì)于5個(gè)月前,深圳市交通運(yùn)輸局將及
深圳交通局官方賬號(hào)禁止網(wǎng)民評(píng)論2023-09-16 16:51:09近日,深圳市交通運(yùn)輸局對(duì)網(wǎng)民申請(qǐng)公開(kāi)北極鯰魚(yú)調(diào)查情況一事作出不予公開(kāi)的回復(fù),很快便引起了社會(huì)大眾對(duì)于5個(gè)月前,深圳市交通運(yùn)輸局將及 -
 軍訓(xùn)順拐同學(xué)們組成了方隊(duì) 引發(fā)了網(wǎng)友們的熱議2023-09-16 16:49:42軍訓(xùn)順拐同學(xué)們組成了方隊(duì)近日,在陜西某高校的軍訓(xùn)場(chǎng)上,一幕引人注目的場(chǎng)景吸引了網(wǎng)友們的目光,教官組建了一支名為順拐方隊(duì)的隊(duì)伍。這支
軍訓(xùn)順拐同學(xué)們組成了方隊(duì) 引發(fā)了網(wǎng)友們的熱議2023-09-16 16:49:42軍訓(xùn)順拐同學(xué)們組成了方隊(duì)近日,在陜西某高校的軍訓(xùn)場(chǎng)上,一幕引人注目的場(chǎng)景吸引了網(wǎng)友們的目光,教官組建了一支名為順拐方隊(duì)的隊(duì)伍。這支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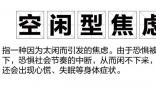 空閑型焦慮困住打工人 不敢休息一閑下來(lái)就心慌2023-09-16 16:45:25或許你聽(tīng)說(shuō)過(guò),有人因?yàn)楣ぷ魈β刀箲],也聽(tīng)說(shuō)過(guò)有人因?yàn)楣ぷ魈y而焦慮,但如今,越來(lái)越多的人,正因?yàn)榭臻e而焦慮。尤其是在一種內(nèi)卷加
空閑型焦慮困住打工人 不敢休息一閑下來(lái)就心慌2023-09-16 16:45:25或許你聽(tīng)說(shuō)過(guò),有人因?yàn)楣ぷ魈β刀箲],也聽(tīng)說(shuō)過(guò)有人因?yàn)楣ぷ魈y而焦慮,但如今,越來(lái)越多的人,正因?yàn)榭臻e而焦慮。尤其是在一種內(nèi)卷加 -
 網(wǎng)紅吳川偷逃稅被追繳并罰款1359萬(wàn) 遂依法對(duì)其開(kāi)展了稅務(wù)檢查2023-09-16 16:38:53據(jù)國(guó)家稅務(wù)總局廣西壯族自治區(qū)稅務(wù)局網(wǎng)站消息,前期,廣西壯族自治區(qū)稅務(wù)部門通過(guò)分析發(fā)現(xiàn)網(wǎng)絡(luò)主播吳川涉嫌偷逃稅款,經(jīng)提示提醒、督促整改
網(wǎng)紅吳川偷逃稅被追繳并罰款1359萬(wàn) 遂依法對(duì)其開(kāi)展了稅務(wù)檢查2023-09-16 16:38:53據(jù)國(guó)家稅務(wù)總局廣西壯族自治區(qū)稅務(wù)局網(wǎng)站消息,前期,廣西壯族自治區(qū)稅務(wù)部門通過(guò)分析發(fā)現(xiàn)網(wǎng)絡(luò)主播吳川涉嫌偷逃稅款,經(jīng)提示提醒、督促整改 -
 恒大人壽嚴(yán)重資不抵債 恒大人壽風(fēng)險(xiǎn)處置再進(jìn)一步2023-09-16 16:37:30恒大人壽風(fēng)險(xiǎn)處置再進(jìn)一步。9月15日,國(guó)家金融監(jiān)督管理總局深圳監(jiān)管局官網(wǎng)公布《關(guān)于海港人壽保險(xiǎn)股份有限公司受讓恒大人壽保險(xiǎn)有限公司保
恒大人壽嚴(yán)重資不抵債 恒大人壽風(fēng)險(xiǎn)處置再進(jìn)一步2023-09-16 16:37:30恒大人壽風(fēng)險(xiǎn)處置再進(jìn)一步。9月15日,國(guó)家金融監(jiān)督管理總局深圳監(jiān)管局官網(wǎng)公布《關(guān)于海港人壽保險(xiǎn)股份有限公司受讓恒大人壽保險(xiǎn)有限公司保 -
 王耀慶因徐良淘汰哭了 這一事件引起了廣泛關(guān)注和熱議2023-09-16 16:35:03在最近的一場(chǎng)演出中,著名演員王耀慶的表演被觀眾們熱烈的掌聲和歡呼聲所淹沒(méi)。然而,當(dāng)他的好友兼搭檔徐良被淘汰時(shí),王耀慶卻因?yàn)楸瘋?
王耀慶因徐良淘汰哭了 這一事件引起了廣泛關(guān)注和熱議2023-09-16 16:35:03在最近的一場(chǎng)演出中,著名演員王耀慶的表演被觀眾們熱烈的掌聲和歡呼聲所淹沒(méi)。然而,當(dāng)他的好友兼搭檔徐良被淘汰時(shí),王耀慶卻因?yàn)楸瘋? -
 金正恩被烏克蘭網(wǎng)站列入專項(xiàng)名單 這是基輔政權(quán)的又一次挑釁2023-09-16 16:33:55據(jù)塔斯社15日?qǐng)?bào)道,對(duì)于烏克蘭名為和平締造者的網(wǎng)站將朝鮮國(guó)務(wù)委員長(zhǎng)金正恩列入專項(xiàng)人員名單,俄副外長(zhǎng)加盧津批評(píng)稱,這是基輔政權(quán)的又一次
金正恩被烏克蘭網(wǎng)站列入專項(xiàng)名單 這是基輔政權(quán)的又一次挑釁2023-09-16 16:33:55據(jù)塔斯社15日?qǐng)?bào)道,對(duì)于烏克蘭名為和平締造者的網(wǎng)站將朝鮮國(guó)務(wù)委員長(zhǎng)金正恩列入專項(xiàng)人員名單,俄副外長(zhǎng)加盧津批評(píng)稱,這是基輔政權(quán)的又一次 -
 女子高鐵座位被占換回后遭3人毆打 鐵路天津西站派出所已介入2023-09-16 16:32:26據(jù)荔枝新聞報(bào)道,近日,在G2610次高鐵上,一女子座位被占,換回座位后卻遭3人毆打。當(dāng)事人李女士介紹,換回座位后,對(duì)方多次對(duì)其座椅進(jìn)行敲
女子高鐵座位被占換回后遭3人毆打 鐵路天津西站派出所已介入2023-09-16 16:32:26據(jù)荔枝新聞報(bào)道,近日,在G2610次高鐵上,一女子座位被占,換回座位后卻遭3人毆打。當(dāng)事人李女士介紹,換回座位后,對(duì)方多次對(duì)其座椅進(jìn)行敲 -
 演員袁冰妍偷逃稅被處罰并追繳297萬(wàn)2023-09-16 16:29:35前期,重慶市稅務(wù)部門通過(guò)分析發(fā)現(xiàn)袁冰妍存在涉稅風(fēng)險(xiǎn),經(jīng)提示提醒、督促整改、約談警示后,袁冰妍仍整改不徹底,加之其關(guān)聯(lián)企業(yè)存在偷逃稅
演員袁冰妍偷逃稅被處罰并追繳297萬(wàn)2023-09-16 16:29:35前期,重慶市稅務(wù)部門通過(guò)分析發(fā)現(xiàn)袁冰妍存在涉稅風(fēng)險(xiǎn),經(jīng)提示提醒、督促整改、約談警示后,袁冰妍仍整改不徹底,加之其關(guān)聯(lián)企業(yè)存在偷逃稅 -
 卓偉爆料古裝劇準(zhǔn)頂流男星將塌房 可能在9月底爆料該明星的瓜2023-09-16 16:27:319月16日,知名娛記卓偉終于現(xiàn)身了,這些年他一直隱身,很少曝明星大瓜了,很多網(wǎng)友紛紛表示,沒(méi)有卓偉的日子,娛樂(lè)圈真的好寂寞,明星的戀
卓偉爆料古裝劇準(zhǔn)頂流男星將塌房 可能在9月底爆料該明星的瓜2023-09-16 16:27:319月16日,知名娛記卓偉終于現(xiàn)身了,這些年他一直隱身,很少曝明星大瓜了,很多網(wǎng)友紛紛表示,沒(méi)有卓偉的日子,娛樂(lè)圈真的好寂寞,明星的戀
必要](http://www.ncxsd.cn/uploadfile/2022/1215/20221215072835405.jpg)